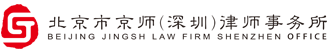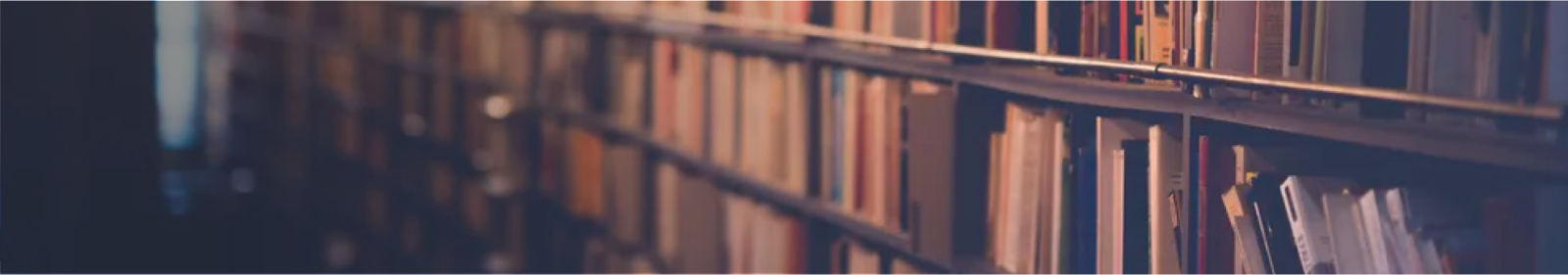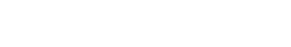本文作者:王喆、廖杰 一 智能合约的定义 “智能合约”一词最早由计算机科学家尼克・萨博(Nick Szabo)于1994年提出,其最初定义为“一套以数字形式定义的承诺,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”。目前广泛认可的智能合约定义为“部署在区块链上的、由事件驱动的、具备自动执行功能的计算机程序,其核心功能是将合约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编码为代码,当预设条件(如时间、交易金额、外部数据)满足时,自动触发相应的履约行为(如转账、资产确权)”。该定义明确了智能合约的技术载体(区块链)、触发机制(事件驱动)与核心功能(自动执行)。智能合约具有三个核心特征:其一,去中心化存储,合约代码与交易数据存储于区块链节点,无单一控制方;其二,不可篡改性,合约部署后除非通过共识机制(如硬分叉),否则无法修改;其三,透明可追溯,所有合约交互记录均公开可查,确保交易公信力。从法律视角来看,智能合约通常界定为“以区块链为技术载体,以代码为表现形式,约定当事人权利义务,并具备自动执行功能的电子合同”。 二 智能合约的法律属性 智能合约的法律属性存在诸多争议,核心焦点集中在“是否属于独立合同类型”“与传统电子合同的异同”“代码条款的法律地位”三个方面: (一)是否属于独立合同类型 部分人认为,智能合约的“自动执行”“去中心化”特性与传统合同存在本质差异,应成为独立的合同类型。智能合约无需第三方中介即可履行,打破了传统合同对“信任机制”的依赖,其法律属性应独立于电子合同,需专门立法规制。 我国主流观点认为,智能合约仍属于电子合同的范畴,无需创设新的合同类型。《民法典》第469条明确“以电子数据交换、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,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,视为书面形式”,智能合约的代码本质上是“有形表现所载内容的数据电文”,符合电子合同的构成要件。 (二)与传统电子合同的异同 智能合约与传统电子合同的共性在于:均以数据电文为表现形式、均需符合合同的成立要件(要约、承诺、意思表示一致)、均受《民法典》合同编规制。但二者存在显著差异,具体如下表所示: (三)代码条款的法律地位 “代码即条款”是智能合约的核心特征,但代码条款与自然语言条款的冲突如何解决,成为法律属性认定的关键,当智能合约同时存在代码条款与自然语言条款时,可能出现“代码执行结果与自然语言约定不一致”的情况(如代码漏洞导致多转账),此时需明确二者的优先效力。对此存在两种观点:其一,“代码优先原则”,认为代码是智能合约的唯一有效条款,自然语言仅为解释说明,因代码的执行结果具有确定性,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;其二,“自然语言优先原则”,认为代码是实现自然语言条款的工具,若代码与自然语言冲突,应以自然语言为准,因代码可能存在漏洞,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。 笔者更倾向采用“区分原则”:若当事人明确约定“代码条款为唯一有效条款”,则优先适用代码;若未明确约定,且代码漏洞导致结果与自然语言冲突,则应以自然语言为准,同时追究代码开发者的过错责任。该原则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,又能防范代码漏洞引发的不公,符合《民法典》“公平原则”与“诚信原则”的要求。 三 智能合约的技术架构 智能合约并非孤立的计算机程序,而是依赖区块链技术的多层级架构体系。根据技术功能的不同,可将其分为区块链底层、合约代码层、应用层三个层级,各层级的技术构成与功能如下: (一)区块链底层 区块链底层是智能合约的技术基础,负责提供去中心化存储、共识机制、加密算法等核心支撑。区块链底层的核心技术组件分为四类:(1)分布式账本:所有节点共同维护一份账本,记录智能合约的部署信息、交易记录与执行结果,确保数据透明可追溯;(2)共识机制:通过算法(如工作量证明PoW、权益证明PoS)实现节点间的信任达成,决定智能合约的执行与账本的更新(如以太坊从PoW转向PoS后,共识效率大幅提升);(3)加密算法:采用非对称加密(如RSA、ECDSA)确保合约主体的身份认证与交易安全,通过哈希算法(如SHA-256)确保数据不可篡改;(4)P2P网络:节点间通过点对点网络直接通信,无需中心化服务器,确保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部署与执行。 (二)合约代码层 合约代码层是智能合约的核心,负责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编码为可执行的计算机程序。目前主流的智能合约开发语言包括Solidity(以太坊平台)、Vyper(以太坊平台)、Chain code(Hyperledger Fabric平台)等,其中Solidity因“图灵完备”“语法简洁”成为最常用的语言。合约代码层的核心组件包括:(1)合约接口:定义智能合约与外部交互的方式(如函数调用、数据输入),确保外部应用(如DApp)能够触发合约执行;(2)状态变量:存储合约的核心数据(如当事人地址、交易金额、履约状态),状态变量的修改需通过合约函数实现,并记录于区块链;(3)函数:实现合约的具体逻辑(如转账函数、条件判断函数),函数的执行需满足预设条件(如“只有合约所有者可调用”“转账金额不超过余额”);(4)事件:当合约执行关键操作(如转账成功、合约终止)时,触发事件并记录于区块链,便于外部应用监听与查询。 (三)应用层 应用层是智能合约的用户交互界面,负责将合约功能转化为具体的应用场景,供用户直接使用。智能合约的应用层分为两类:(1)去中心化应用(DApp):基于智能合约开发的前端应用,用户通过DApp与智能合约交互(如DeFi平台Aave的借贷DApp,用户通过界面输入借款金额,触发底层智能合约执行);(2)第三方服务:为智能合约提供辅助功能的服务,如预言机(提供外部数据)、代码审计机构(检测漏洞)、存证平台(保存合约证据)等。 四 智能合约的运行流程 智能合约的运行流程可分为编写、部署、触发、执行、终止五个阶段,每个阶段的技术操作与法律意义如下: 阶段一:合约编写(法律上的“要约起草”)。开发者根据当事人的需求,使用Solidity等语言编写智能合约代码,明确合约主体(区块链地址)、权利义务(如借款金额、还款期限)、触发条件(如“还款日期到期”)、执行结果(如“自动扣划还款金额”)等内容。此阶段对应的法律行为是“要约起草”,当事人需对代码内容进行确认,确保其符合真实意思表示。编写过程中需避免代码漏洞,如重入攻击(未对转账顺序进行限制)、整数溢出(未对金额范围进行校验)。 阶段二:合约部署(法律上的“要约发出”)。开发者将编写完成的合约代码编译为字节码,通过区块链节点提交部署请求,并支付一定的“Gas费”(区块链网络的运行费用)。区块链网络通过共识机制验证部署请求后,将合约字节码存储于区块中,并生成唯一的“合约地址”(类似银行账号)。此阶段对应的法律行为是“要约发出”,合约内容通过区块链公开,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。合约部署后,代码不可修改(除非通过硬分叉),因此需在部署前进行多次测试。 阶段三:合约触发(法律上的“承诺生效”)。合约当事人或第三方(如预言机)通过调用合约接口,输入触发条件所需的数据(如“还款日期已到”的时间数据、“商品已签收”的物流数据),触发合约执行。若输入数据满足预设条件,合约将自动执行;若不满足,则执行失败。此阶段对应的法律行为是“承诺生效”,当事人通过触发行为表示接受合约条款,合约正式成立。触发数据的真实性至关重要,尤其是依赖外部数据的智能合约(如供应链合约需物流数据)。 阶段四:合约执行(法律上的“履约行为”)。合约触发后,将自动执行预设的函数逻辑,如向指定地址转账、更新状态变量、触发事件等。执行结果将被记录于区块链,并同步至所有节点,确保不可篡改。此阶段对应的法律行为是“履约行为”,合约义务通过代码自动履行,无需当事人手动操作。 阶段五:合约终止(法律上的“合同终止”)。当合约预设的终止条件满足(如“所有义务履行完毕”“合约到期”)或当事人通过共识机制(如DAO投票)决定终止时,智能合约停止运行,状态变量冻结,合约地址不再接受新的触发请求。此阶段对应的法律行为是“合同终止”,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。部分智能合约未设置终止条件,可能导致“永久运行”。 五 智能合约的主要应用领域 (一)去中心化金融(DeFi)领域 DeFi是智能合约最核心的应用领域,智能合约在DeFi中的应用场景包括借贷、交易、衍生品、流动性挖矿等,其核心优势是“无需中介、实时结算、透明可追溯”。例如在Aave借贷平台,用户通过智能合约抵押数字资产(如以太币),即可自动获得贷款,无需银行审核;还款时,智能合约自动扣划还款金额与利息,并解除抵押资产的冻结。Aave的智能合约采用“超额抵押”机制(抵押率通常为150%),当抵押资产价格下跌至平仓线时,合约自动平仓,降低坏账风险。 (二)供应链管理领域 智能合约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,主要解决“信息不对称”“流程繁琐”“信任缺失”等问题,通过代码自动记录商品的生产、运输、仓储、销售等环节,实现全流程透明可追溯。例如沃尔玛与IBM合作,基于Hyperledger Fabric区块链平台开发智能合约,记录食品的产地、检测报告、物流信息等数据。当食品出现质量问题时,智能合约可自动追溯至责任环节,并触发赔偿流程(如向消费者自动退款)。(如物流企业不愿共享数据,供应链智能合约则面临“数据孤岛”问题)。 (三)知识产权领域 智能合约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,主要包括版权确权、授权使用、收益分配等场景,通过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确保知识产权的真实性,通过智能合约自动实现授权与分润。例如Music Coin音乐版权平台,音乐人将作品上传至平台后,智能合约自动生成版权证书(含区块链哈希值),完成确权;用户购买音乐时,智能合约自动将费用按预设比例分配至对应账户,无需中介机构(如唱片公司)参与。 (四)公益捐赠领域 智能合约在公益捐赠中的应用,主要解决“资金挪用”“透明度低”等问题,通过代码明确捐赠资金的使用范围与条件,当条件满足时自动拨付资金,确保专款专用。例如支付宝蚂蚁链公益平台,捐赠人通过平台捐赠资金后,智能合约将资金冻结,仅当受赠方完成预设目标(如“为贫困儿童购买1000件棉衣”)并上传证明材料(如物流单据)时,合约自动解冻资金并拨付给受赠方;若未完成目标,资金自动退回捐赠人。(建议公益智能合约引入“第三方审计条款”,由独立机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)。 六 智能合约的潜在风险 (一)潜在技术风险 代码是智能合约的“法律条款”,但代码编写过程中存在的“技术认知局限”,直接导致漏洞产生。包括开发者对编程语言特性不熟悉(如Solidity中的“默认可见性”问题,函数未指定可见性时默认“public”,导致任何人可调用)、逻辑设计错误(如The DAO事件中的“先转账后更新状态”)、测试不充分(仅进行功能测试,未进行安全测试)。编程语言本身的缺陷(如Solidity0.7.0版本前无内置溢出检查)、开发工具的漏洞(如早期Truffle框架的编译错误)、区块链平台的兼容性问题(如不同平台对合约函数的执行逻辑差异)。例如2022年Axie Infinity Ronin桥事件,开发者因未理解“跨链合约的权限隔离机制”,将“验证节点私钥”与“转账合约私钥”存储在同一服务器,导致黑客通过一次攻击获取双钥,窃取6.25亿美元资产。由于智能合约代码的“不可修改性”,一旦存在漏洞,如重入攻击¹、整数溢出² 、权限控制漏洞³ 等,黑客可利用漏洞窃取资金,且难以通过技术手段挽回损失。 去中心化区块链的吞吐量受限于“节点共识效率”,如以太坊PoS升级前的吞吐量仅为15笔/秒,远低于传统支付系统(如Visa的2000笔/秒)。交易高峰期时,智能合约因“Gas费竞争”导致延迟,甚至执行失败。例如,2021年DeFi热潮期间,以太坊Gas费峰值达500Gwei(约合150美元/笔),大量小额智能合约因用户不愿支付高额费用而无法执行,引发“合约触发失败”。 预言机作为“区块链与现实世界的接口”,若提供虚假数据(如伪造物流信息、操纵价格数据),将导致智能合约执行错误,引发纠纷。例如,2020年11月,Compound平台因Coinbase提供的DAI价格数据异常(从1美元暴涨至1.34美元)触发大规模清算。 (二)潜在法律风险 1. 智能合约效力认定 智能合约是否符合《民法典》规定的“合同生效要件”,尤其是“意思表示真实”“内容合法”两个要件。代码条款是否构成“意思表示”?部分观点认为,代码是技术工具,并非当事人的意思表示,智能合约不具备合同效力;主流观点认为,代码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“数字化载体”,若代码内容与当事人真实意愿一致,智能合约应认定为有效。涉加密货币智能合约的效力方面,由于我国禁止加密货币的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活动,涉加密货币的智能合约是否因“内容违法”而无效,存在争议。 2. 缔约主体认定 智能合约的缔约主体通常以“区块链地址”表示,而区块链地址具有匿名性,无法直接对应真实身份,导致纠纷发生时“当事人主体资格认定”困难。具体争议包括:如何证明某区块链地址的实际控制人是某自然人或法人,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;若区块链地址由他人代理操作,如何认定代理关系,是否构成表见代理。 3. 条款解释争议 智能合约通常存在“代码条款”与“自然语言条款”两种表现形式,当二者内容不一致(如代码执行结果与自然语言约定冲突)时,如何解释合约条款,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。具体争议包括:代码条款与自然语言条款冲突时,应以哪一种为准;若代码条款存在歧义或漏洞,且无自然语言条款补充,如何依据法律原则填补漏洞。 4. 专门法律供给不足 我国对智能合约的监管分散在网信、金融、工信等多个部门,缺乏统一的监管框架。新兴场景无规可依,NFT、元宇宙、AI智能合约等新兴场景,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则。如NFT智能合约中的“权利归属”“侵权认定”,目前只能参照《著作权法》《民法典》的类似条款,无法精准适配。假设某艺术家(甲方)创作一幅画作,委托平台(乙方)通过智能合约发行NFT,合约约定“NFT购买者仅享有收藏权,不得用于商业用途”。某企业(丙方)购买该NFT后,将其用于产品宣传(商业用途),甲方起诉丙方侵权,要求赔偿;丙方辩称“智能合约未在监管部门备案,合约中‘禁止商业用途’的条款是否有效不明确”,主张免责;乙方则认为“自身仅提供技术服务,不承担侵权责任”。在缺乏NFT专项监管规则的情况下,合约中“权利限制条款”是否具有法律效力?乙方作为NFT发行平台,是否需对丙方的侵权行为承担“监管义务”(如提醒丙方权利限制)? 5. 传统救济方式适配性问题 智能合约的“自动执行”“不可篡改”特性,导致传统司法救济方式(如禁令、撤销、执行)难以发挥作用,具体表现为:(1)禁令救济失效,传统合同中,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发布禁令,禁止对方违约行为(如禁止擅自转移资产),但智能合约的执行由代码自动触发,一旦条件满足,立即执行,法院无法及时发布禁令阻止。(2)撤销与变更困难,传统合同可因“重大误解”“欺诈”被撤销或变更,但智能合约执行后,结果记录在区块链,不可篡改,即使法院判决撤销,也无法删除链上记录,只能通过“赔偿”弥补损失,无法恢复原状。(3)执行难度大,智能合约纠纷的执行标的多为数字资产,且数字资产具有“匿名性”“跨境性”,法院难以查询、冻结、扣划。 6. 跨境法律适用问题 智能合约的“跨境性”导致法律适用难度显著高于传统合同,主要体现在:(1)跨境纠纷的冲突规范适配难,传统合同纠纷的管辖权通常依据“被告住所地”“合同履行地”,但智能合约的“履行地”难以确定(如合约部署在全球节点,交易在链上完成)。(2)准据法选择难,当事人未约定准据法时,法院需依据“最密切联系原则”确定,但智能合约的“密切联系点”(如节点所在地、开发者所在地、用户所在地)分散。不同国家/地区对智能合约的监管态度差异显著(如欧盟认可DeFi智能合约的合法性,我国禁止加密货币相关合约),导致跨境智能合约(如跨境借贷、跨境贸易)可能面临“一地合法、一地违法”的困境,引发合约效力、执行范围的争议。假设某欧盟企业(甲方)与美国企业(乙方)通过以太坊智能合约签订跨境借贷协议:甲方以USDC(稳定币)向乙方出借100万美元,期限6个月,乙方以ETH作为抵押,合约约定“适用欧盟法律,争议由伦敦国际仲裁院(LCIA)管辖”。借款期间,美国SEC将该类借贷合约认定为“未注册证券发行”,禁止在美国境内执行;乙方据此拒绝还款,主张合约在美国违法,应终止履行;甲方认为合约适用欧盟法律,且已在欧盟合法备案,乙方应继续履行。合约在欧盟合法是否意味着在美国也需履行?美国的监管政策是否构成乙方的“履约抗辩事由”?若LCIA裁决乙方还款,该裁决能否在美国执行(因美国认为合约违法)? 七 智能合约风险解决的技术自治机制 智能合约的技术自治机制,是指依托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与代码可编程性,通过预设技术规则实现风险的自主识别、预警与化解,无需依赖第三方中介(如法院、仲裁机构)的干预。其核心逻辑是“代码即治理工具”,将风险解决规则嵌入合约架构,实现“风险触发-规则执行-结果落地”的全流程自动化,体现区块链“去中心化自治”的本质属性。 从价值定位来看,该机制弥补了传统风险解决方式的效率短板与信任成本。技术自治机制使智能合约风险解决的响应时间从传统司法的“月级”缩短至“分钟级”,且无需当事人对第三方建立信任,尤其适配区块链去中心化生态。例如,DeFi协议中常见的“自动清算机制”,可在抵押率触及风险阈值时立即执行资产处置,避免风险扩散,这一过程无需人工干预,完全依赖代码逻辑自治。 同时,技术自治机制与智能合约的“不可篡改”“透明可追溯”特性深度契合。风险解决规则一旦部署上链,所有节点均可验证规则的合法性与执行过程,避免暗箱操作;执行结果记录于区块链,不可篡改且可追溯,为后续争议提供明确证据,这种“透明化自治”显著降低了风险解决中的信息不对称,提升用户对机制的信任度。 根据风险解决的功能差异,智能合约风险解决的技术自治机制可分为风险预防型、风险处置型、争议裁决型三类。 (一)风险预防型自治机制:源头规避风险触发 风险预防型机制通过预设技术规则,从源头降低风险发生概率,核心包括“代码安全自治”“权限控制自治”“数据验证自治”三类子机制。 1. 代码安全自治机制 依托形式化验证、自动漏洞扫描等技术,在合约部署前自主检测代码风险,通过数学逻辑证明代码是否符合预设安全规则(如转账逻辑、权限边界),可自动识别重入攻击、整数溢出等高危漏洞,避免漏洞引发后续纠纷。 2. 权限控制自治机制 通过多签权限、角色隔离等技术,限制单一主体对合约的操控权限,预防权限滥用风险。典型架构为“多签钱包+角色权限映射”:核心操作(如修改合约参数、提取资金)需多个管理员地址共同签名(如3/5多签,即5个管理员中至少3人同意),且不同角色(如开发者、用户、审计员)仅拥有对应权限(如审计员仅可查看数据,不可修改参数)。例如,Compound协议的“治理多签合约”,所有重大参数调整需通过社区投票+多签确认。 3. 数据验证自治机制 针对预言机数据错误风险,通过多源数据聚合、去中心化节点验证等技术,自主确保输入合约的数据真实可靠。例如,Chainlink预言机通过1000+节点组成的去中心化预言机网络(DON),对加密货币价格数据进行自治验证。 (二)风险处置型自治机制:触发后快速化解 当风险已发生(如抵押率跌破阈值、合约漏洞被利用),该机制通过预设代码逻辑自动执行处置措施,降低损失扩大风险,核心包括“自动清算机制”“紧急暂停机制”“资产转移机制”。 1. 自动清算机制 在DeFi借贷、衍生品等场景中,当用户抵押资产价值低于预设阈值(如150%抵押率),合约自动触发清算逻辑:出售部分抵押资产以偿还债务,剩余资产返还用户,避免债务违约风险。例如,Maker DAO的DAI稳定币合约,当ETH抵押率低于150%时,合约自动将抵押ETH在Uniswap上挂单出售,清算过程无需人工干预。 2. 紧急暂停机制 当检测到异常交易(如大额异常转账、合约漏洞被利用),合约自动或通过社区投票触发“紧急暂停”,冻结合约所有功能,防止损失扩大。典型实现为“异常检测模块+暂停开关”:异常检测模块实时监控合约调用频率、转账金额等指标,触发预设阈值(如单次转账超合约总额50%)时,自动发送暂停请求;若需人工干预,社区可通过投票激活暂停开关。 3. 资产转移机制 当合约存在不可修复漏洞(如权限控制失效),通过预设代码将用户资产自主转移至安全合约地址,保障资产安全。该机制需满足“多签授权+透明追溯”要求,转移过程的所有记录均上链,确保用户知情权。 (三)争议裁决型自治机制:去中心化解决纠纷 当风险引发当事人争议(如预言机数据错误导致的损失分担),通过DAO治理、智能合约仲裁等去中心化技术,自主裁决争议结果并执行,核心包括“DAO投票裁决机制”“智能合约自动仲裁机制”。 1. DAO投票裁决机制 由持有治理代币的社区成员组成DAO(去中心化自治组织),通过投票决定争议解决方案(如损失赔偿比例、责任归属),投票结果通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。典型流程为:①当事人提交争议证据(如链上交易记录、技术鉴定报告);②DAO成员对证据进行质证并投票;③投票通过后,合约自动执行裁决(如从过错方地址扣划赔偿款至受损方地址)。 2. 智能合约自动仲裁机制 将仲裁规则编码为智能合约,当争议发生时,合约自动提取链上证据(如合约条款、交易记录),依据预设规则(如“预言机数据错误属第三方责任”)作出裁决,并直接执行结果。该机制无需人工参与,完全依赖代码逻辑,适用于简单争议(如违约认定、赔偿金额计算)。例如,区块链仲裁平台Kleros的“智能合约仲裁协议”,通过“陪审团+代码规则”结合的方式,2023年处理400余起智能合约争议,平均裁决时间24小时。 (四)技术自治机制的局限性 技术依赖风险:自治机制自身存在漏洞。技术自治机制的运行依赖代码与区块链基础设施,若机制自身存在漏洞,可能引发“二次风险”。 决策公平性不足:少数主体掌控话语权。在DAO投票裁决机制中,治理代币的集中持有可能导致“少数人决策”,损害普通用户利益。当前多数DAO的“一人一票”实为“一币一票”,代币集中化导致决策公平性不足,与技术自治机制的“去中心化”初衷相悖。 强制力缺失:违约主体难以约束。技术自治机制的执行依赖当事人的“代码遵从性”,若违约主体拒绝执行裁决(如不配合资产转移、利用技术手段规避清算),机制缺乏有效约束手段。 注释 作者介绍 王喆律师 北京市京师(深圳)律师事务所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联合创始人、基金债券法律业务中心主任 业务领域: 资产证券化、投资并购、争议解决 执业经验: 王喆律师曾为中建八局、中建六局、山东电建、商丘发投、商丘新城、平煤集团、河南路桥、海通恒信、首创置业、京能国际等公司提供资产证券化法律服务;为中海油、华润置地、华润医药、万科地产、北燃集团等企业提供投资并购法律服务;为平安信托、招商信托、国投泰康信托、中诚信托等提供信托法律服务;为汇丰银行、恒生银行提供内保外贷、开发贷等法律服务;为北燃蓝天、国投瑞银、信达资产等提供争议解决法律服务。 王喆律师主办的中国中投证券-德远保理-中建八局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于2019年荣获“2018-2019年度资产证券化介甫奖”,该项目系首单交易所储架发行的、以央企为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,对传统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进行了多项优化,实现了多层次的创新和突破;王喆律师主办的天星数科-粮票供应链10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荣获2022年第六届CNABS资产证券化最具行业影响产品奖。 廖杰律师 北京市京师(深圳)律师事务所律师、基金债券法律业务中心成员 业务领域: 资产证券化、争议解决 执业经验: 廖杰律师具备法律与会计双学位,曾为中国电建、商丘发投、商丘新城、山东电建、京能集团、曲江资本、平煤集团、河南路桥、潍坊城投、济南城投、潍坊三农、颐养健康等公司提供资产证券化法律服务;为鄂尔多斯东胜**煤矿投资纠纷案等提供争议解决法律服务;曾在企业长期从事法务工作,为集团及下属公司的业务提供日常法务支持,负责集团下属公司私募基金及资管产品投资事宜。